为什么在国外烤面包,在中国则成了蒸馒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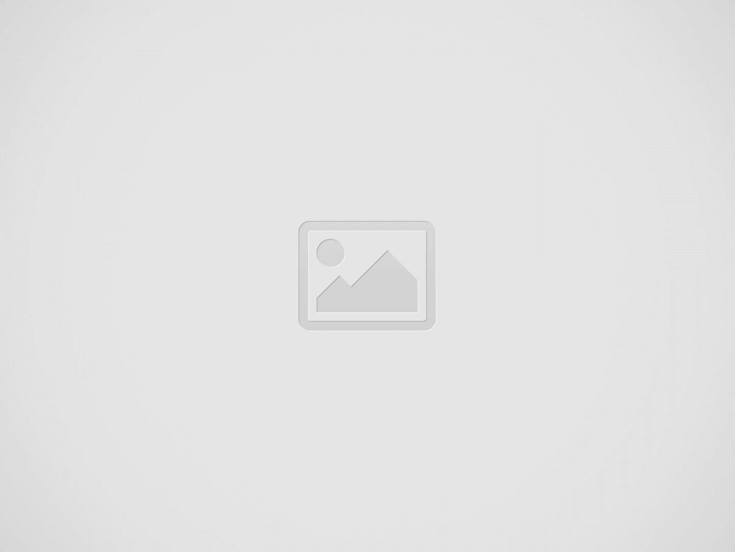

作者:艾栗斯
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4月18日)
面包在欧洲作为主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的地位只能算作点心或小食。与古埃及人早早发明了面包不一样,中国是直到明朝万历年间,面包的制作技术才由传教士利马窦和汤若望第一次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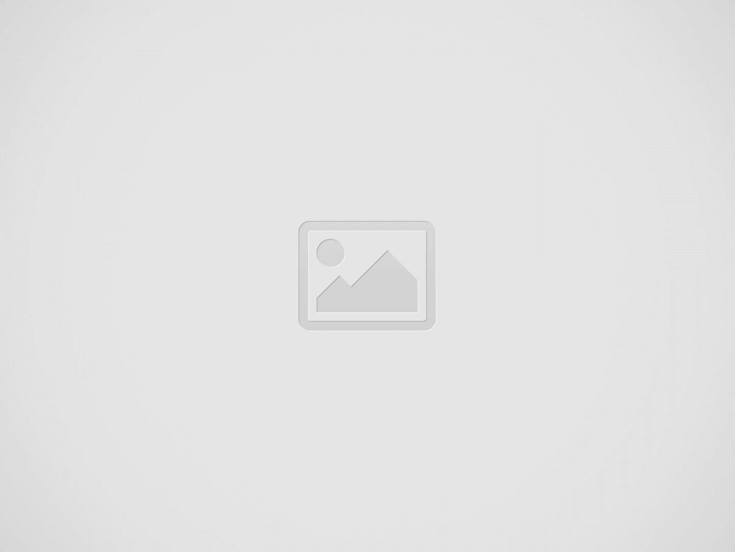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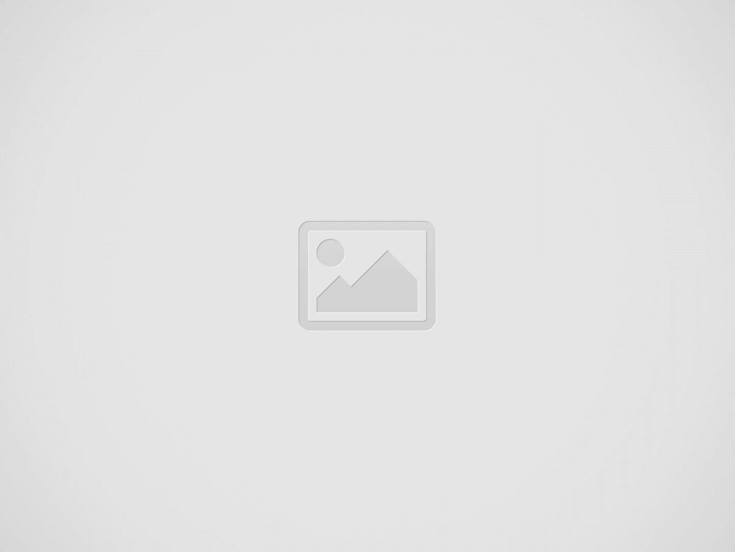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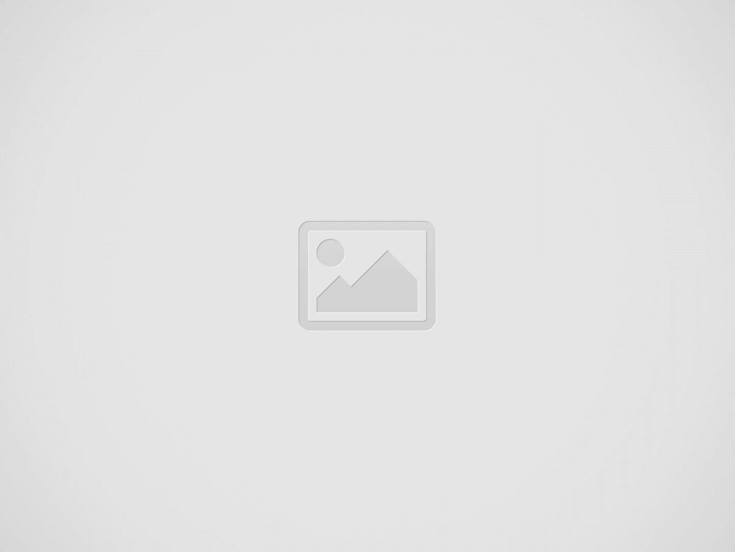

今天刷着手机在“网红”面包店前排起长队的人们也许难以相信,面包这种看似新潮的舶来品究其历史竟然已经有七八千年。手捧松软香甜面包的人们可能也不会想到,使面粉蓬松柔软的“魔法”,最早来自古埃及。
古埃及——阴差阳错产生发酵面包
面包的出现几乎与农业文明曙光同步。因为带有坚硬外壳,收获后的小麦难以即时食用,必须去壳磨成面粉,制成小麦粥和薄饼聊以充饥。是谁第一个突发奇想,将稍加研磨的麦粉加水拌成糊状,放在烤热的石板上制成薄饼?味道又如何?问题的答案已难觅其踪,只能从中东地区仍延续类似做法的烤饼上一作窥探,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未经发酵的烤饼即是面包的原型,在它诞生后差不多过了两千年,才被古巴比伦人带入埃及。
尼罗河水定期泛滥,掌握自然规律以后,埃及人却因此得到了肥沃耕地。肥沃耕地上生长出的小麦,不仅是尼罗河水的意外馈赠,也是农耕文明里丰收的象征——埃及丰饶女神伊西丝的头上即有一把小麦标志的装饰迎风招展。在埃及人手里,小麦面包经历了一次决定性的飞跃,从无发酵面包一举成为发酵面包,也奠定了今天面包的两大基本分类。而在面包华丽转身背后,却是一次遗忘之后,时间给予的惊喜。
用石头磨碎小麦外壳的工作相当艰巨,一次尽可能多磨面粉,多揉面饼,可以喂饱更多人。某次辛苦劳作后,一份多余的面饼被烹饪者遗忘在角落,暴露于尼罗河畔的高温下,与空气密切接触了一整天。没人注意到犄角旮旯里有个面团正在噗噗冒泡膨胀,独自迈向食物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等到第二天再被想起时,面饼已经大了一号,火烤以后既有蓬松的口感更具谷物的香气,既更饱腹也更易消化。
彼时彼地的埃及人还不知道,这种神奇的变形源自面粉麸质与空气作用释放出的微生物:野生酵母——人类通过显微镜看到酵母菌的存在还要等到5000多年后的维多利亚时期。如尼罗河一样,埃及人同样把面包的新做法看作神的恩赐。就这样野生酵母侵入生面团,阴差阳错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发酵面包。埃及人如法炮制将更多的面团暴露在空气中,更加娴熟地制作起发酵面包来。
顺带的,他们还发现面包烤制前的液体初筛后也可以用来填饱肚子,所以最早的啤酒又被称为“液体面包”。面包,啤酒,一个普通埃及人的主食就是以上两者。数千万建造古埃及金字塔的工人们以面包为口粮,维持体力、应付繁重劳作。这样看来,说“金字塔是建造在数以万计面包上”也不算夸大——威廉·基尔在《面包的历史》一书中就曾提到:“古埃及仆人一整年的工资报酬是三百六十杯啤酒、九百个白面包、三万六千个普通面包”、“法老外出时,会携带数万个面包供国王和随行者食用。”
埃及人无比珍惜神赐的面包,将其作为敬奉神明的供品,他们还发明了最早的烤炉。放在薄石头上隔火烤的方法从埃及时期开始变为送进烤炉,面包的式样、种类、口味也随之开始递增:圆形、立方形、麻花形、动物形……五十多种不同形状的面包让人眼花缭乱。面包制作在埃及成了一门手艺,面包也成就了除金字塔外埃及人的特征——留存的木乃伊中可以看出,古埃及人牙齿普遍欠佳,现代医学认为原因就在于他们吃了太多的面包,造成了磨损和糖分残留。当时的外族人也觉得埃及人吃了太多的面包,他们看着这为面包狂热的民族,将埃及人称为“(神选)吃面包的人”。
古希腊罗马——面包成为餐桌上的顶梁柱
伴随贸易往来,发酵面包由埃及传到希腊。与埃及人一样,希腊人认为其饮食的三大构成:谷物、橄榄油以及葡萄酒是众神赐予的三样礼物。其中雅典娜教会希腊人种植橄榄、葡萄酒来自酒神狄俄尼索斯、谷物则是女神德墨忒尔的馈赠,希腊的各类菜肴都以以上三者为基准,这也与只吃肉喝羊奶的游牧民族区分开来。
埃及人已经忘记了发酵面包的发明者,但是希腊历史上却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一位名叫忒亚里翁的雅典人,他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是商业面包房的首创。如此掐指一算,今天我们在街角看到的面包店原来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比咖啡馆、理发店以及其他零售店的历史都要久远。
除了埃及人的小麦面包,希腊人的面包房里还可以买到黑麦面包、谷物面包、白面包(精筛面粉制作)、未筛粗粉的全麦面包;在面粉中添加橄榄油、猪油、葡萄酒、牛奶、蜂蜜、罂粟花、芝麻,以及干果、奶酪等辅材……各项排列组合下,面包制作方法已达七十多种。
对于面包的欣赏是一种朴素而知足的希腊式生活方式。在希腊的贵族宴会上,高高垒起的面包通常放在藤编的篮子里呈上,正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记载:“帕特罗克罗斯从漂亮的篮里拿出面包,放在台子上,分给每一张餐桌。”
罗马人接过希腊人面包制作的接力棒,又额外添加了两个贡献:一是专注于技术改进的罗马面包师发现,酿造啤酒的酵母液可以被提取出来专门用做面包的发酵工序,使烤出的面包更加松软可口。直到中世纪晚期,欧洲人还在使用罗马时期的啤酒花酵母法制作发酵面包。
罗马人的另一个杰出贡献,是把“吃面包”变成了一项公共事务。现代人虽然有了厨房和家用烤箱,但大量的面包消费还是在面包店进行,这与古希腊罗马的情况如出一辙。相比希腊人,罗马人更是将城市里的面包坊利用到极致——早在公元前100年,罗马城的面包店就已经达到250家,店里的面包师经过职业培训,批量生产的面包不仅是罗马市民维系生命的能量来源、精神愉悦的抚慰,也是罗马公共生活的基础。古罗马市民习惯将磨粉、过筛、揉面、发酵、烘烤的繁琐工序交给专业的面包师,既免去了自己没有厨房和工具烹饪的尴尬,也省下大把时间用作广场的高谈阔论。有的面包师会在广场中设有公用的烤炉,各地送来的面团在这里集中烤制,作为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福利成批出品并且免费配给罗马市民。
难怪古罗马人说自己文明的两大支柱是“面包和竞技”,背后其实是罗马执政者的统治之道——以面包填饱市民的肚子平息矛盾,以罗马场竞技吸引市民的精神转移注意力。免费的面包虽然没有维持罗马帝国的永久统治,却开启了面包作为普罗大众餐桌上的顶梁柱的地位,以及面包的欧洲化传播之路。
为什么在国外烤面包,在中国则成了蒸馒头?
面包在欧洲作为主食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的地位只能算作点心或小食。与古埃及人早早发明了面包不一样,中国是直到明朝万历年间,面包的制作技术才由传教士利马窦和汤若望第一次传入。
麦子和石磨这两样东西都源于中亚,几乎同时出现。早在公元六千年前两河流域的人就将小麦磨成面粉,揉成薄饼后放在石板上烤;而在小麦传入到中国时,烹饪的工具已经不是石器而是陶器甚至青铜。
在烹饪技术上,古代中国大量地使用蒸、煮这两种方式——稻米在火上烤会焦煳,烤炙法只是游牧民族的习惯,从来都不是农耕文明高度发达的华夏民族饮食主流。可以说,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隔水蒸熟食物的技艺,食材不直接接触火或水,而是用热气蒸熟。
东方烹饪的智慧将面粉带上了另外一条路,在小麦传来时也自然将面饼放入陶锅中蒸,这就成了蒸出来的馒头而非烤出来的面包。但在没有面包的东方岁月里,面粉并不孤独。馒头里加入五花八门的馅料如青葱、鲜肉、青菜、豆沙甚至糯米,就产出了各色嫡生:花卷、包子、烧麦。不发酵的面皮加入不同馅料就成了饺子、馄饨或汤圆。另有一团面粉被切片或拉伸以后直接与沸水接触,汤水间成就了全国各地的各种面条——在有关面团的美味上,中华料理显然更有想象力。
中世纪——面包的多重“寄语”
蛮族入侵、古罗马时代结束,公元5世纪起,欧洲拉开了中世纪的序幕。兵荒马乱中,繁琐的面包制作工序几近奢侈,欧洲人多以燕麦粥和饼充饥。直到公元6世纪,乡间才陆续有简陋的炉火被支起,面包开始在家庭中烹饪作为主食。与古罗马时代相比,欧洲人采用的是一样的炉火(大部分时候更为简陋)、一样的酵母(啤酒花酵母极其珍贵);不一样的是面包的供给关系:城市消亡了,变成零星散落的乡村,罗马城市公共基础的面包提供被乡间小作坊或家庭手工替代。负责面包粉的磨坊与烘烤面包的作坊常为一家,闲暇时面包作坊的烤炉以收费形式,向家中无力搭起炉火的村民们开放。
不一样的还有罗马市民难以体会到的饥饿感。在水稻、玉米、小麦这三大谷物中,小麦的产量最低,而从9世纪起到14世纪,日益增长的欧洲人口又越来越依赖谷物,这就意味着中世纪的面包往往成分复杂。大麦、燕麦、黑麦、栗子以及其他谷物豆类,只要是能想到的,都会被拿来磨粉做成面包充饥,哪怕最终成品是坚硬无比、难以下咽的“黑面包”。黑面包这种粗粮面包可以长期储存,即使过期,也会被磨碎加入酱汤中增稠饱腹。而对于富裕家庭来说,无论现烤现买,吃的都是小麦制成的新鲜白面包。吃什么样的面包,就代表什么阶级。
由于关系到国计民生,面包师是中世纪最早诞生的职业之一,欧洲各国对于面包价格的管理也都非常严格。公元630年,法国达戈贝特一世出台了第一条控制面包价格的法令;1266年,英国的“面包与麦酒”法令里规定了每便士能买到的面包数量。缺斤少两、以次充好的面包师会受到严厉惩罚,轻则处以四五十倍的罚金,重则封闭炉门、终身禁入面包行业。
从中世纪起,面包不仅是一日三餐果腹必须,更富有西方文化的象征意义。一方面,面包与宗教紧密联系,在《圣经》里提到的面包,近一半与神灵有关。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说:“面包是我的肉,葡萄酒是我的血。”因此在天主教的圣餐仪式中,面包必不可少。
1666年,伦敦普丁大街上的一个面包作坊里,小伙计在临睡前忘记熄灭零星的炉火,火苗顺着风势蹿出炉门,酿成伦敦历史上最大一次火灾——三天三夜的大火将伦敦80%的建筑毁于一旦,但伦敦也在余烬的原地进行彻底重建,成为欧洲金融城。又一次与面包有关的阴差阳错,将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带入了新时期。
工业革命——面包在科技进步中波折发展
今天80%以上的面包都来自工厂机器生产,但人类历史上机器的轮轴刚开始运转时,却是面包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页。
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迎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潮水般的人口涌进城市的工厂和街道,吃住都在狭窄的生活空间解决。过去那种耕种在农地,产出谷物自给自足烤制成面包的关系链条业已断裂。告别了田园牧歌式的面包坊经营,血汗工厂隔壁即是血汗面包作坊。
如果说中世纪穷人的黑面包难以下咽,那么维多利亚早期的面包则是有损健康。一磅重的面包在1838年相当于工人一天的工资,用脚投票的低购买力消费者与数量众多面包坊间的恶意竞争,使得面包食品造假成风:过期面粉、土豆粉、豌豆粉,以及其他包括白垩粉甚至明矾都被掺杂在面包粉中——如今城市中产阶级推崇的健康粗粮谷物面包,在当时却是被鄙弃的穷人食物。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就记录了维多利亚时代消费者对于面包的需求:“越白越好,越便宜越好”——白垩粉加入,为的是面包能吸收更多的水分以虚增重量,而明矾,则是为了使面包外观看起来更像高级的“白面包”。
伴随大生产而来的不光有无序竞争,还有对新技术的恐惧。19世纪50年代,英国面包工人掀起了抵制机器进入面包坊的运动,法国科学家路易·巴斯德在古埃及人发明了发酵面包几千年以后,终于借助显微镜看清了面包里酵母菌的真身。但是巴斯德一派却认为,既然酵母属于一种活动真菌,那么也跟其他有害细菌一样,与广泛的疾病传播脱不开干系。一时间对于酵母“细菌”的恐慌让欧洲一度摒弃了发酵面包,因为酿酒同样经历发酵过程,所以禁酒令也随之流行。
恰逢在科学的显微镜下,又一种新物质被发现: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可以融入水中,带有强烈工业感的苏打水由此诞生。最早生产出的苏打水被广告商包装成有益健康的药品,这给了一家面包公司以灵感。他们尝试放弃酵母,将二氧化碳压进水里的技术应用到面粉里,制造出了不依靠酵母就能膨胀的气体面包。“充气面包”带着新时期满满的科技感,体积比原先更蓬松,也无需担心“酵母细菌”,然而看似完美的面包尝起来总像是缺失了什么——口感空洞,缺少酵母的香气。没过多久消费者的新鲜劲退去,昙花一现的“充气面包”就因缺少人情味而被抛弃。
好在从19世纪中后期起,科技进步的力量终于惠及到了面包坊。1851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吸引了六百多万观众,怡泉公司凭着40分钟内可以生产400多个面包的机器,为参观者提供了934691份小圆面包。制作面包的机械一个个出现,宣布了现代烘焙业的诞生:1870年,调粉机出现;1880年,面包整形机被发明;1888年,电烤炉代替了蒸汽烤炉……到了19世纪80年代,机器磨粉能达到石磨从未实现的精细程度,由于铁路运输兴起,面粉和糖的价格大幅下降,低价吃到货真价实的白面包或是糖、油丰富的花式面包已不是难事。不过随着食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在众多的选择面前欧洲人的面包消费却只有从前的1/4,面包在欧洲独一无二的主食地位逐渐被土豆、肉类、玉米等瓜分,但“爱情还是面包”这样的俚语依然常常被人们引用,彰示着面包曾经的地位。
(本版部分图片来自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