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路下段2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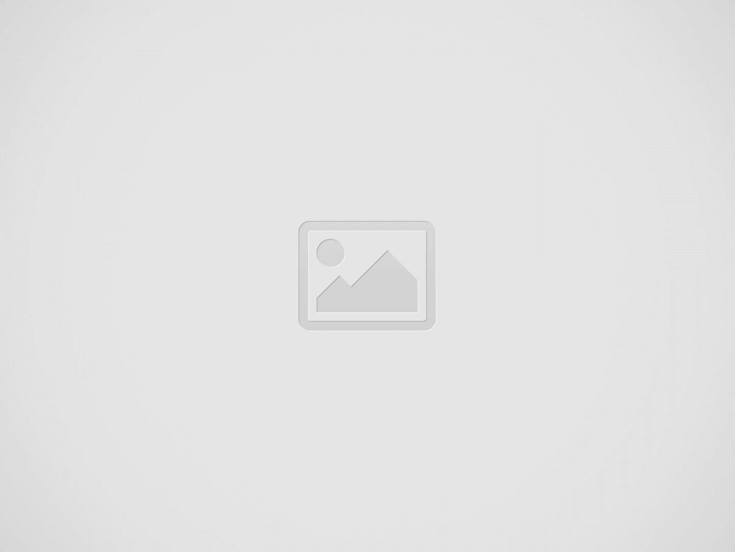

在飞机上写小作文真的是再好不过的消磨时间的方式了。因为最近在大理晃了两天,所以还有得可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没什么质量可言,我写了,痛快了,就完了。
我的朋友羽凡跟我说:“在大理,哪个客栈没点儿故事”
羽凡是个上海人,上学时漂在天津,后来漂在大理,时不时回趟上海。我觉得他会说中国范围内的全部方言,有着超乎寻常的语言天赋,在中国说方言可是比说洋文更招人喜欢。我和他就是他漂在天津时认识的,其实八杆子打不着,但一直到现在都有着一种微妙的联系。因为只要路过,无论是上海还是大理,我都得找他玩上一会儿。
我到大理出差,顺便留在大理放空赋闲两天,就住进了他住的客栈。
一个小小的院子,两排小楼,我住在靠里面的二楼,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把排风口给通错了地方,在屋里就能闻到楼下做饭的烟火味。
楼门口拴着一只叫初九的狗,明明是一只只有三岁的金毛,却长了一对巴吉度的眼睛,下眼睑往下耷拉着,眼睑内部血色旺盛,看上去孤独、绝望,除了吃以外,没有任何狗子应该有的欲望。
前段时间又被拿去割掉了命根子,变得更没有欲望了,整天的吃喝拉撒都在院子里解决,在半夜总是没有缘由地狂叫。
“哎,可怜的初九” 他抬起头拿那对巴吉度眼睛看了看我,又趴了下去,我觉得他得有十几岁了。
狗子旁边有一个长长的实木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最大尺寸的苹果PC机,旁边还配着两条长长的实木椅子,靠着狗子这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穿着棕色皮夹克的中年男子在看电影,桌子的另一头放了一瓶1.75L的占边和一个摆着几只小羊茶宠的茶海。
中年男子叫小铭,一个在大理开客栈的酸腐文人艺术家,才华布满了客栈的每一个角落,画的画和写的字完全是可以拿出来得瑟得瑟的水平。但这位爷最近爱上了打牌,24小时去三次牌局,有时还拿客栈拿来卖的咖啡换筹码。在我看来这种生活状态实在难以饶恕,才华难道不是需要拿出来得瑟的吗,怎么能随便扔在哪让它长毛呢。
小铭之前是知名4A公司的设计师,在北京上班时也住十里堡,在很早以前还是我现在住的小区的业主,可惜房价还没爆表的时候就把房子出手了,来大理开了客栈。这笔账现在也不敢算了,一提到北京现在的房价就有点泪光闪闪的。
拿在北京时的生活背景和小铭凑了近乎之后,我得到了蹭客栈午饭、拿他电脑看电影和去他牌局搂一眼的机会。好吧,其实是因为羽凡,他和小明认识好多年了。
我就很羡慕羽凡这种到哪都能交上朋友的人。我基本上一直处于一个无法社交的状态,抽冷子时才可能跟人敞开心扉地聊两句,但也只是两句而已。我觉得我有一定程度上的自闭,没人知道我想的什么,我自己有时都不知道。
我又看了一眼初九,居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来小铭这里的第一天,我们三个人一直喝到半夜三点,从吃饭时就开始喝。米酒就烤肉、花生就占边,1.75L的占边一晚上就给干没了。羽凡喝多了就开始说各种方言,看到隔壁打麻将的云南大婶也能跟人家对付两句;小铭喝多了开始给我安利他的牌局,并且终于让我参观了他的洋葱头和半边脸,都关于孤独和爱情,两个困扰着全人类的主题。
洋葱头是他画的一个脑袋是一个洋葱头的小人儿,整体有些梵高的色调,小人儿有时坐在鲸鱼上,有时从花丛里跑出来,形单影只,可怜巴巴的。半边脸是一堆人捂着一边脸的照片,大概也是寻找另一半的意思,每个人只是一半的自己,只有找到了另一半才算得上是个完整的人。
看完了画我觉得舒坦了,确定了我们差不多是一类人之后继续喝。羽凡估计是为了陪陪我这个刚来的,一直撑到半夜三点。在北京可没人陪咱这么待着,就算待着了也是聊工作、抱怨房租以及谁又跟谁搞在了一起。我努力睁着大眼睛,抱着他们不说结束我就不主动上楼睡觉的决心硬撑,这毕竟太奢侈了。
住在大理的外来人基本有两个状态,不是本来就没什么欲望,就是已经没什么欲望了。我在大理的这两天虽然也喝了酒、溜达了,但也是一直抱着电脑打着电话,电话里依旧聊着工作和臭钱。
还好,在大理待了两天之后,我还是那个我,对金钱有着巨大欲望的我。临走之前我还兴致勃勃地去打听了松茸渠道,准备在来年捞上一笔呢。